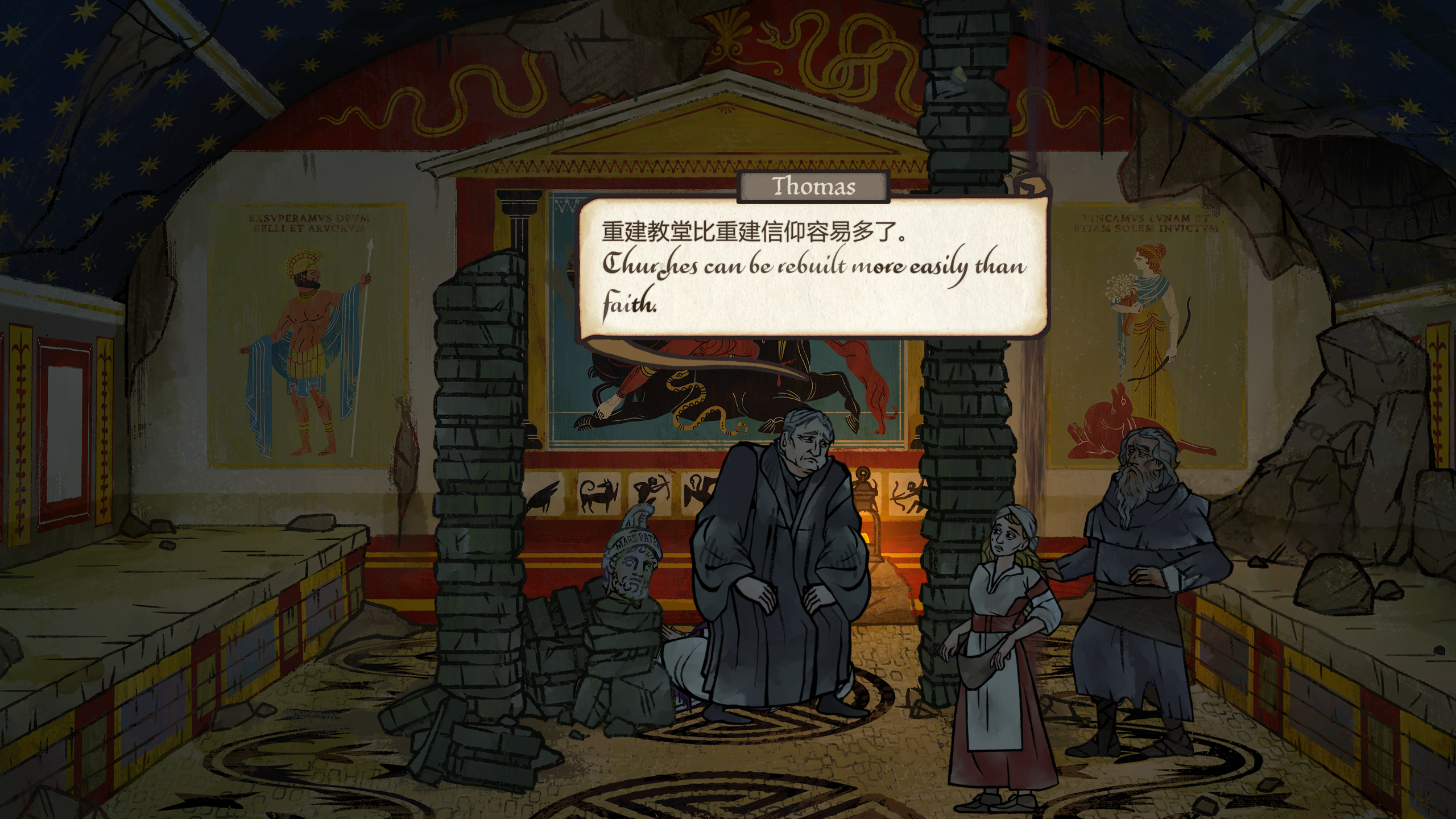引
最开始听说这个游戏,是第一次准备考研时想要找《极乐迪斯科》那种剧情好并且可以学英语的代餐,我原本以为我找不到了,但是我在社交平台上还真找到了(忘记是小红书还是小黑盒了)。这个游戏如果打上玩家自制的补丁的话就可以实现中英双语阅读,甚至比极乐迪斯科还要友好,因为极乐迪斯科每次切换语言都要一小段延迟,而这个没有。并且这个游戏在xpg上也有,但是因为考研的时间日益紧张,我玩了开头的五分钟就再也没玩了,当时觉得这种文艺复兴的手绘风看不惯,
两年后我再次抱着学习英语的目的打开这个游戏时,是因为我的xgp订阅只剩下两周半的时间,我本想着去玩暗喻幻想,但是暗喻幻想实在是太无聊了,老套的剧情和狗屎的迷宫和简陋的战斗系统丝毫没有让人玩下去的欲望。于是乎我点开了这个游戏,不料一发不可收拾,惊讶的发现自己又找到了一个神作。
悬疑?
在游戏的开头,我们扮演这一个远道而来的画师,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给塔兴大教堂画画来打工。不出意外的,大教堂的赞助商在来的时候遇害了,于是我为了避免自己的挚友遇害,不得不去试着找出真凶,于是一个悬疑的侦探游戏拉开了序幕…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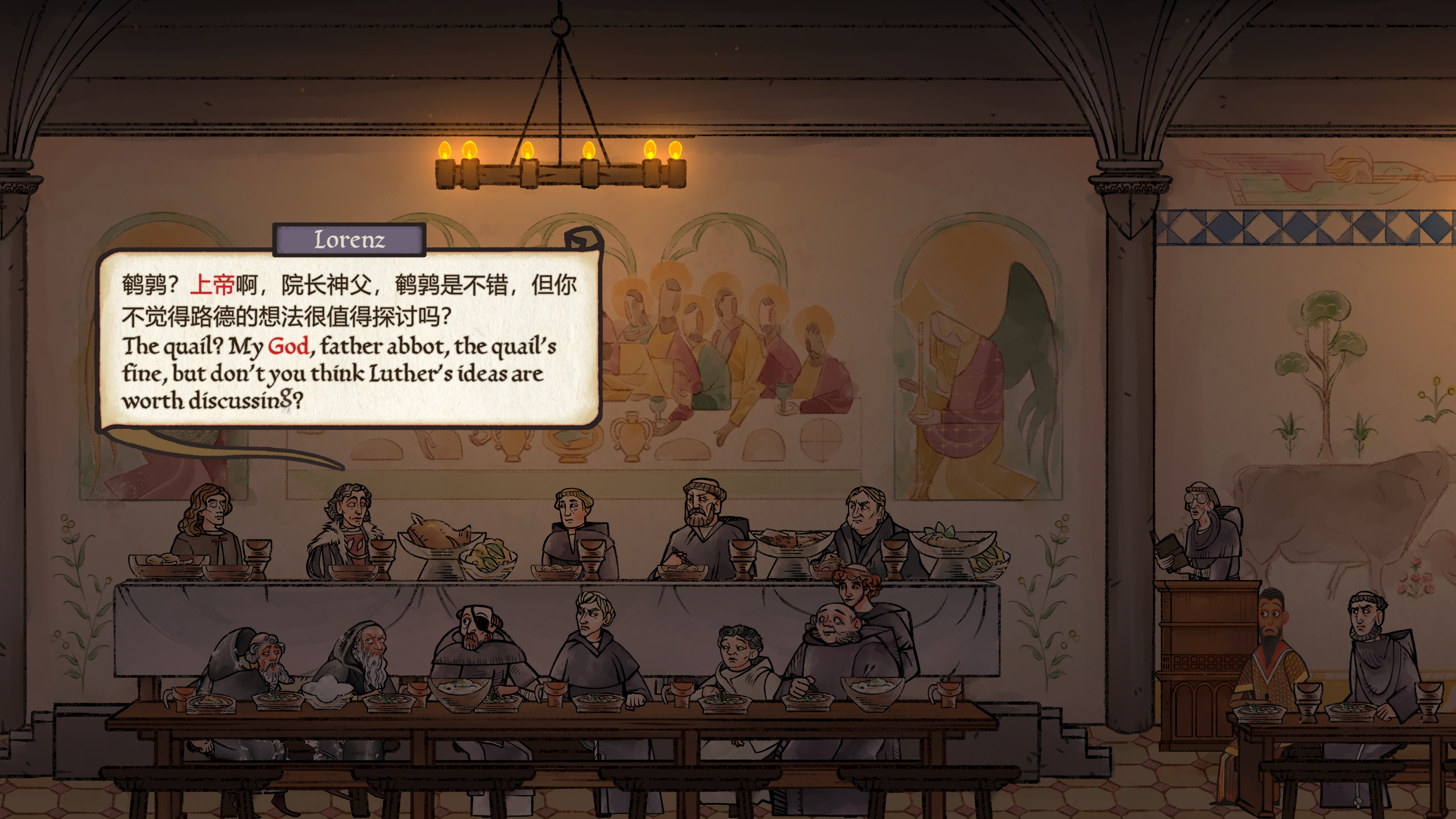
并非如此,游戏通过对话来收集线索,而收集线索需要时间。整体属于网状叙事,需要从各方调查来查清 真相。但是,游戏并没有给我充分的时间,事实上,你根本不可能在一次把所有的剧情全部集齐,起码要多几个周目才行,在我偷偷从图书馆回来的那个晚上,就在我还在回味捕捉到长老和修士搞基的乐子时,游戏告诉我:会吏官来了,我必须开始指控一个人了。
指控?我如何指控?我虽然手里有一些线索,但是我并没有决定性的证据。但是我还是得硬着头皮指控了我最讨厌的长老,我以为会吏官会再给我几天时间找到真凶,但是并没有,几分钟后主教被押到广场,斩首示众。第一幕结束了。
我感到有些难以置信,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游戏并不是一个常规的推理悬疑游戏,因为你可能根本没找到真凶!你只是为了保护好人而把其他一些有罪的人推了出去罢了。到了第二幕,时间更加紧凑,我只能抓住一条线索,最后把那个和磨坊主偷情的女人推了出去。我感到悲伤但是又无可奈何,我悲伤因为我不确定我推出去的人是否是真凶,我无奈是因为我必须推一个出去,院长不是好人但是我知道他的确不是真凶,我因为可怜的正义感需要找到真凶,但是我却指控一个我不确定是真凶的人。何其悲哀。
再第三幕的结尾,当我看到神父在大伙聚会离开的时候,我的心中对于真凶是谁,已经有了答案,但我也知道,真凶的身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动机,为什么?
宗教
宗教是这个游戏绕不开的话题,感谢汉化,不然如果让我硬啃这些宗教名词和地名我肯定啃不下来。游戏对于宗教的描写不至于基督教,还涉及到了原住民的原始信仰,罗马人的信仰和后来被基督教取代的历史,对于这些异教的着墨也是谜题的迷底。
在讨论基督教前,我先聊聊自己在游玩前对于基督教的看法。我认为基督教还是有一些积极作用的,比如通过辩经推进了科学和哲学的进步,传播了基本的普世道德观,维护了基层的安定。但是对于基督教的消极作用,得益于娱乐作品长时间的刻板印象的宣传我对于他的消极作用还是缺乏更加现实的认识。但是在游戏中,基督教在历史中的影子被很好的还原了,值得细说。
塔兴镇的建立和基督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传言出过两个圣人,其中一个圣人的手臂还作为圣物供奉,这让基督教徒来塔兴朝圣,间接的带动了塔兴的旅游业,也让大教堂可以富丽堂皇,并且有缮写室,使得我们的主人公可以来塔兴打工,可以说,这个虚构的传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塔兴的繁荣,使得我们可以在塔兴看到形形色色的人。
但是,维护大教堂需要开支,尤其是缮写室和图书馆,这两个是开支的大头,他们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维持着文化的传承,可又不得不靠剥削这农民维持。不经如此,院长的日常饮食还很丰盛,就在开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寄宿的农家告诉我他们因为上涨的税收而欠了大教堂的钱,恳请我提前支付房租。兵器在吃饭的时候提到了他们最好的白面粉都要给大教堂。第二幕在我去院长家吃饭时也能注意到,院长吃的都是白面包,院长的房间更是豪华(讽刺的是,院长的房间有两个门,一个可以从镇上直接进去,而一扇需要从教堂绕一大段,第一扇门似乎一直都是关着的),甚至连的狗都膘肥体壮。而与此同时农夫家里的人得了病,却连面包都吃不起,哪怕是去树林拣点吃的都不被允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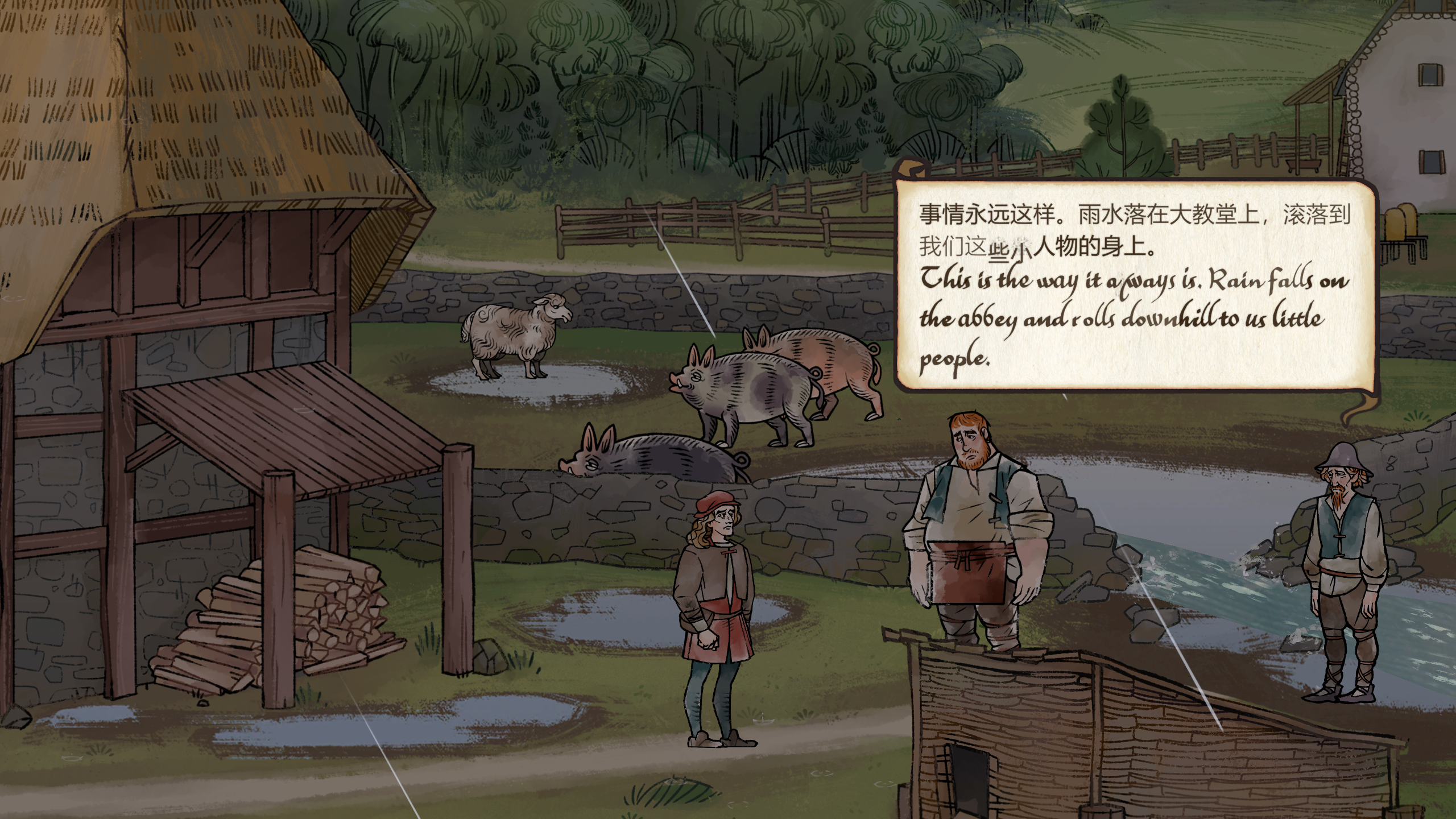
大教堂如此鱼肉百姓,对吗?显然不可能,游戏发生的十六世纪末期宗教改革已经拉开了序幕,主角甚至可以和路德上同一所大学,路德宗的思想也传播到了塔兴这个小镇,大教堂内部的一些人也对新思想抱有开明的态度,甚至就连大教堂的赞助人这种食利阶层都对路德的思想感兴趣,更别提广大农民了。在第二幕,院长加重税收,于是印刷商把反对苛政的《十二条款》印刷传播,不识字的木匠站起来号召人们反抗暴政。后来我才知道,游戏中提到的《十二条款》是真实存在的,德意志帝国的农民在这个时期对于暴政的反抗也是真实存在的。
第二幕的主题是关于革命,我们的主角作为一个艺术家,在阶级的划分上属于中间派。这使得他可以同时接触到上层和下层的看法。主角一方面同情农民的吃不上饭的悲惨遭遇,一方面又希望保全大教堂里图书馆的书籍从而认同教堂剥削的合理性,但是我不能决定剧情的大走向,那个演讲的木匠必然被人陷害,愤怒的农名必然冲入大教堂烧毁一切,而在那之后又被雇佣兵残酷的镇压。值得讽刺的是大教堂的僧侣中就有着一个曾经是雇佣兵的人,不知道他看到雇佣兵杀害平民的时候会想什么呢?雇佣兵是外国的,对于他们来说帮助他国镇压暴乱可以说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甚至还会因为维护了领主和教会的通知得到赏赐,哪怕暴乱的原因就是这些权贵的挥霍无度,何其讽刺!这么来看也许大一统的国家推翻上层的统治可能性更大。
在革命之后,富丽堂皇的大教堂被烧为废墟,大部分僧侣和修士也离开了这个小镇。基督教的统治开始减弱,但是,那个曾经和长老偷情的修士居然当上了会吏长,我想不到宗教人员居然可以直接担任政府的实权人员,看来我之前低估了宗教在欧洲社会中的地位。并且在第二幕中我们可以得知,大教堂还需要替领主收税,所以当农民开始抗议教会时,公爵才会出兵镇压。于是封建地主和宗教构成了压迫着小老百姓的两座大山。不知道中国古代的宗教是否会有类似的作用。
人民
游戏中对于无产阶级的描绘大都是偏向正面而且善良的,尤其是在第二章被强制在农夫家里吃饭的那一段,农夫已经穷的连黑面包都吃不起了,家里的孩子和妻子都还身患疾病,即使如此,他们依旧把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给主角吃,哪怕主角比他们富有的多。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一种朴实而坚韧的力量,我没想到这种力量不仅存在于中国历朝历代的无产阶级身上,也存在于西方的无产阶级上,尽管这只是游戏的描写,我也愿意相信在真实的历史中这样的人是广泛存在的。作为对比,我国现在的文娱产业的工作者却致力于描写底层的人性黑暗,不愿相信存在于人民心中的善良,把自己内心的龌龊安在无产阶级的头上,简直无耻。
游戏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阶层的职业。人数最多的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其次是教会的僧侣的修女。年龄分布从小孩到老人都有。我们能看到在第一幕还在牙牙学语的丫头在第二幕开始帮自己的父母干活,你问他还认不认得自己的时候她只会迷茫的摇摇头,然后在第三幕嫁人成家生娃,甚至孩子的名字都是第一幕主角的名字,连猫狗都有自己的孩子。你能看到在第二幕羞涩的石匠在第三幕成功和那个自己喜欢的外地女孩结婚生娃,你能看到主角第一幕被偷(其实是明着拿的)的帽子在第二幕被打了个补丁戴在头上,然后在第三幕又打了个补丁传给了自己的孩子。曾经有点呆傻的大个子后来成为了镇上的议员,在最后的圣诞节发表演讲。在听证时不给你好脸色的会吏官成为了路德宗的信徒还写信给第三幕的女孩来还原当时的真相。使劲变迁,城郭如故人民非。去教堂的草地上出现了靠着朝圣者营业的旅馆,烧毁的大教堂远处建起了镇议会,时代在变迁,小镇也在进步(笑)。
在革命结束后,不同人对于革命的评价都不一样,有的人认为流血冲突就不该发生,他们认为死了这么多的人什么都没改变是很不划算的,哪怕镇议会成立了,他也认为“老爷们还是在压迫着我们,雇佣兵还是在压迫着我们”。但是大部分人对于革命还是保持着积极的态度,认为教会离开、磨坊主的死和镇议会的成立是个好的开始。
写到这里,我开始思考游戏中的磨坊主属于什么阶层。教会不接受粮食抵税,农民需要把小麦拿去磨坊加工成面粉然后卖掉。农民告诉我如果收成好,磨坊主就会上调磨麦子的价格,但是收成差缺不会降回来。在木匠在广场发表反对压迫的演讲时,磨坊主却跳出来说这群人不过乌合之众,领主的雇佣兵可以轻易的把他们图的一干二净,看来磨坊主也是压榨着农民的一份子,甚至可以说是那个年代资产阶级的缩影。在游戏中和磨坊主对话中可以感受到磨坊主对于农民的不屑,在第二幕农民要被饿死了磨坊主甚至还邀请主角和他一起去打猎,而此时农民连进森林拣点栗子都不被允许,因为“森林是领主和教会的财产”。但是磨坊主身为剥削阶级的一员,却没有足够的武力来武装自己不被农民打死,虽然他那奢华的家中摆着一把来福枪,但是面对愤怒的人民,一把来福枪又能如何呢?当第一声枪响打死了镇中的好人乌里奇时,农民点燃了风车,磨坊主被烧死在了风车里,没有武装的资产阶级终究不过是纸老虎罢了,领主的雇佣兵可不会帮你。
虽然讲了这么多磨坊主的坏话,但是磨坊主的儿子带着他的母亲出逃后在几年后又回来了,不仅再次成为了磨坊主,还成为了镇议会的一员。他与他爹的不同之处就是价格公道了,不剥削农民了,镇上的人也不会把他爹的罪过推到他身上,可能是因为他爹已经被清算的缘故。但是这样的情况又能持续几代人呢?无从得知。有时我想,如果他爹没有被清算,或者没有被那些农民亲手清算,那么他儿子的日子还会好过吗?哪怕他儿子确实是个好人?多半不可能,父债子偿嘛。
成立的镇议会,原本的双修修道院只剩下女修道院,那么收税的职责交给了谁呢?毫无疑问是议会,好在议会刚刚成立,还没有腐败的现象。但是在第三幕中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议会的人尽管从小镇中产生,但是还是得要对领主负责,在主角绘制壁画的时候就有不少人担心会引发领主的不满,看来担心因为自己的作品得罪上面而被砍头的现象不是老中独有的。
在第三幕主角换人了,玩家感情深厚的主角在游戏的中途死了而新的主角是从没见过的人,这个剧情怎么在《33号远征队》见过呢?观察社区的评论发现没人讨厌这点,甚至不少人在发现已经死去的主角原来没死后还会非常感动,这么一看这种操作其实没什么值得诟病的地方。
主角死而复生这一点其实有点扯,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能靠着农民扔掉的黑麦苟活。前面才说农民被剥削的要饿死了,难道革命完之后死了太多人然后粮食反而足够了?或者苛政确实宽容了?也许都有吧。但是看到主角在门后出现的时候,确实是让人始料不及,我以为这个人真正的幕后凶手,谁能想到是一个死人呢?但是还是有一点疑惑,为什么苟活了十八年才发现了地道,而且非得等到这一天才带新主角查明真相,早干嘛去了呢?所幸游戏已经快要结束了,这点剧情上的小瑕疵也没人在意。
游戏的真相还是黑了一手基督教,塔兴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原来是建立在一场误会上,甚至所有来朝圣的人都被蒙在鼓里。就好这口荒诞主义的结尾,然而我们无法得知镇上的人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了,也不知道未来的塔兴又将如何,那个失去了朝圣者的旅馆又将如何维持下去。但是这种故事在现实中无数次的上演过,不是吗?